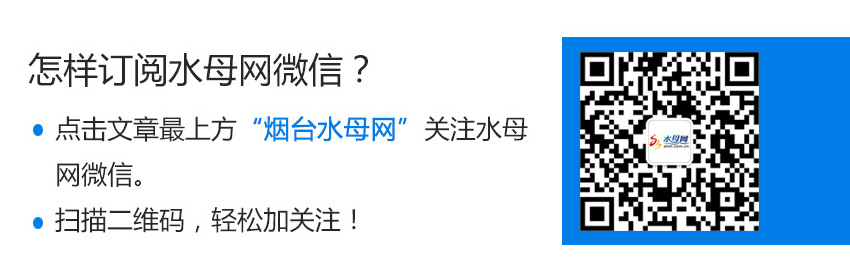乡下牌桌上的娘们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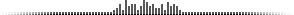
文/冯德良
眼下的乡村,土地大都流转了,剩下的一些零星地块上的活儿,去地里溜达的时候,顺手也就捎带着干完了,于是,人们便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。那些丈夫常年在外打工挣钱,家里闲下来的女人们,除了仨一簇、俩一团站在街上嗑瓜子、看风景、听新闻,议论村里的大事小情,交换手中的“情报”,最喜欢的就是打牌,而且乐此不疲。这是她们的快乐源泉,街道谁家院墙上的乡村振兴标语已经褪色了,也该轮到她们振兴牌技了。
头脑灵活一些的年轻人,喜欢打麻将,她们往往专注于手中的十三张牌,熟能生巧,一些人不用看牌,只用手摸就能分辨出是筒、条、万,如果摸出牌能杠后开花,准会啪叽往牌桌上一拍,开心地大叫一声:“糊了,杠后开花,一百零八!”那副得意忘形的样子,让其他三位牌友立马成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“狐狸”。
人老心不老,生活才美好。最有趣的还是那些上了岁数的乡下妇女打牌。她们如同被时代列车甩下的乘客,会使用的也就是一部老年手机,无法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;看电视,剧中的许多镜头很辣她们的眼睛。只有打起牌来,在哗啦啦的牌响声里,她们在牌桌上或者“忆苦思甜”,或者畅谈心事,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,精神才不至于空虚。她们头脑反应迟钝,记性不好,砸“骨牌”简单些,最适宜她们玩。不过呢,三十二张牌,张张也就有了故事。
这些人打牌不指望着发大财,其实她们也发不了大财。这些喜欢泡在牌桌上的女人们,她们四个人兜里的钱加在一起,可能还没有某个不当家的男人藏在手机壳里的私房钱多呢!她们从儿子或者女儿偷偷摸摸给的零钱中,抽一张出来,换成毛票,怀揣着走向牌桌,牌桌上有的是五角、一角的硬币找零。而剩下的那些钱,则卷在一起,藏在枕头中,缝在被子里,放进鞋子内,塞进老鼠洞,也可能裹上塑料布埋在院子里,以备不时之需。其实真需要时往往又想不起来藏在了哪里。所以,一旦有老人病重或者去世,儿媳们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翻箱倒柜、翻枕头、撕被子,希望能发一笔大财。挖地三尺后往往还真能找到一些,随后便会因为分配不均大打出手,被乡亲们笑话。
牌桌上赢来的“银毫子”是舍不得花掉的,存放于专门缝制的口袋中,宁愿给孙子、外孙大额钞票,也不乐意谁动她那口袋中的碎银子。如果谁从她钱袋子里拿了三五枚硬币,就像动了她的心肝宝贝儿。去牌场或者回家的路上,抖一抖袋子,里面硬币那哗啦啦的响声,别提多么悦耳动听了,这声音让她们精神饱满,斗志昂扬。有输有赢,一年到头,她们袋子里的钱既不会增加多少,也不会减少多少,人生的趣味,就藏在这日复一日的生活里,这些喜欢打牌的娘们的乐趣,就在牌桌上那哗啦哗啦的牌声里。
生活显本色,牌桌见心性。有的人赢钱时非常“谦逊”,有些人输钱时非常“从容”。有些人则不然,喜怒于色,赢了,眉开眼笑;输急眼了,脸涨成了猪肝色,连地上的草棒都不顺她眼。如果抓来了一张杂五(在我们这边是最差的牌),别说两张了,气急败坏,往桌子上一摔,那张牌就飞出三丈之外(大多还是自己捡回来),其他人被惊得张飞穿针——大眼瞪小眼!只是把牌甩出去也罢,还像被人踩住尾巴的小狗一样直叫唤,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。挨打的狗去咬鸡——拿别人出气,你手气差,那张牌何罪之有!
有的女人精神空虚,用打牌来消磨时间,她们比上班的员工打卡都准时,到点就开始。老江湖了,在牌桌上细细地观察着对手,其他三家每个人的一举一动、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,她都能精准地捕捉到这些细节,然后通过心算来判断其他人手中的牌面,那摸牌、出牌、赢牌的感觉真爽,要的就是开心,图的就是快乐。合牌的时候,某个人打了个喷嚏,什么“鼻子痒,有人想”“一个想,两个说,三个是冻着”,酸的、辣的、荤的等油腻的话语就飘散在空气里,紧接着你捶我打,嘻嘻哈哈,乱作一团。
牌桌上也不是一直平静的,老娘们打牌,虽然不至于发生“世界大战”,局部战争时常发生。有时为了一张牌该不该出,为了五毛钱给没给,一言不合,会争吵得面红耳赤,随之,声音越来越高,情绪越来越激动,如同炸毛的公鸡,你一嘴我一嘴,互不相让。人争一口气,佛争一炷香,王八争鲜能熬汤,大小是赌博啊,不是三五毛钱的事,说的是理。要不是牌友们拦住,牌桌的腿说不定就要朝上了。最后有人还发誓说这辈子再也不跟另一个人打牌了,用不了三天时间,两人又坐在同一张牌桌上了。
有的娘们压根就不是为了打牌,纯粹是为了找到一个演讲的平台。从坐下到散场,她会牢牢地掌握着话语权,别人休想插进去说上几句。自己的重孙子都上学前班了,自己还像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中李铁梅奶奶那样“痛说革命家史”,向大家倾诉生活中受到的憋屈。当年分家另过的时候,公婆偏心,把自己喜欢的那个和面盆,偏偏给了老二家。有时候又像祥林嫂一般,絮叨着当年生产队长依仗家族人多势众,如何欺负她家,摘棉花,别人家的女人塞进裤腰里几把,狗腿子、哈巴狗妇女队长视而不见,而她刚放进去一点点,却当着大伙的面搜了出来,如同光着屁股爬城墙——丢人现眼,还得站在那儿让大家品头论足。说到激动处还不忘补上一句:“奶奶个腿,队长家的后人现在还不如俺呢!”她积攒了大半辈子的话题多的是,谁也甭想拦住她的话头,踩着矮板凳上屋顶——你就搭不上言(檐)。有心不和她在一起打牌,她很积极,饭碗一放,早早地坐在了那儿,低头不见抬头见,抹不开面子,只得坐下,然后饱受折磨。
村里乱不乱,牌桌上的娘们儿说了算。她们一边打牌,一边斜着眼睛盯着路人,嘴里说着东家长西家短。看问题的角度不同,一样的眼睛,不一样的看法;不一样的嘴,就有不一样的说法。谁人背后无人说,谁人背后不说人?如果谁把嘴巴凑近了另一个人的耳朵,坏事了,准是“锦衣卫”在交换情报——无外乎谁家的媳妇偷人,谁家的闺女又离婚了,这次找的男人很有钱,只是岁数大点——比她父亲岁数大点……讲的人眉飞色舞,听的人听得津津有味。这些人偏偏忘了那句老话“福自言生,祸从口出”,因为这些碎嘴的娘们无事生非,把没影的事传得有鼻子有眼,有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的起因、经过和结果六个要素俱全,一次次闯祸,以致有人发誓要掀翻她们的牌桌!
乡村生活充满了平淡真实的烟火气,这烟火气源于市井百态、鸡鸣犬吠、炊烟袅袅、地头地边的争吵、骂街声阵阵,也源于这些打牌的娘们无尽的琐碎故事。乡村烟火气,也是调料佐料,让乡下人的生活有滋有味。
作者简介:

冯德良:菏泽市作家协会会员,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,挣过工分,干过临时工,卖过菜,扛过枪,中学高级教师退休。陆续在《太阳雨文学》发表文章近五十万字,诗歌、散文、寓言散见于《当代散文》《青岛文艺》《前卫文艺》《菏泽日报》《牡丹晚报》《牡丹文学》《菏泽作家》《东方文学》……